師范院校“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的幾點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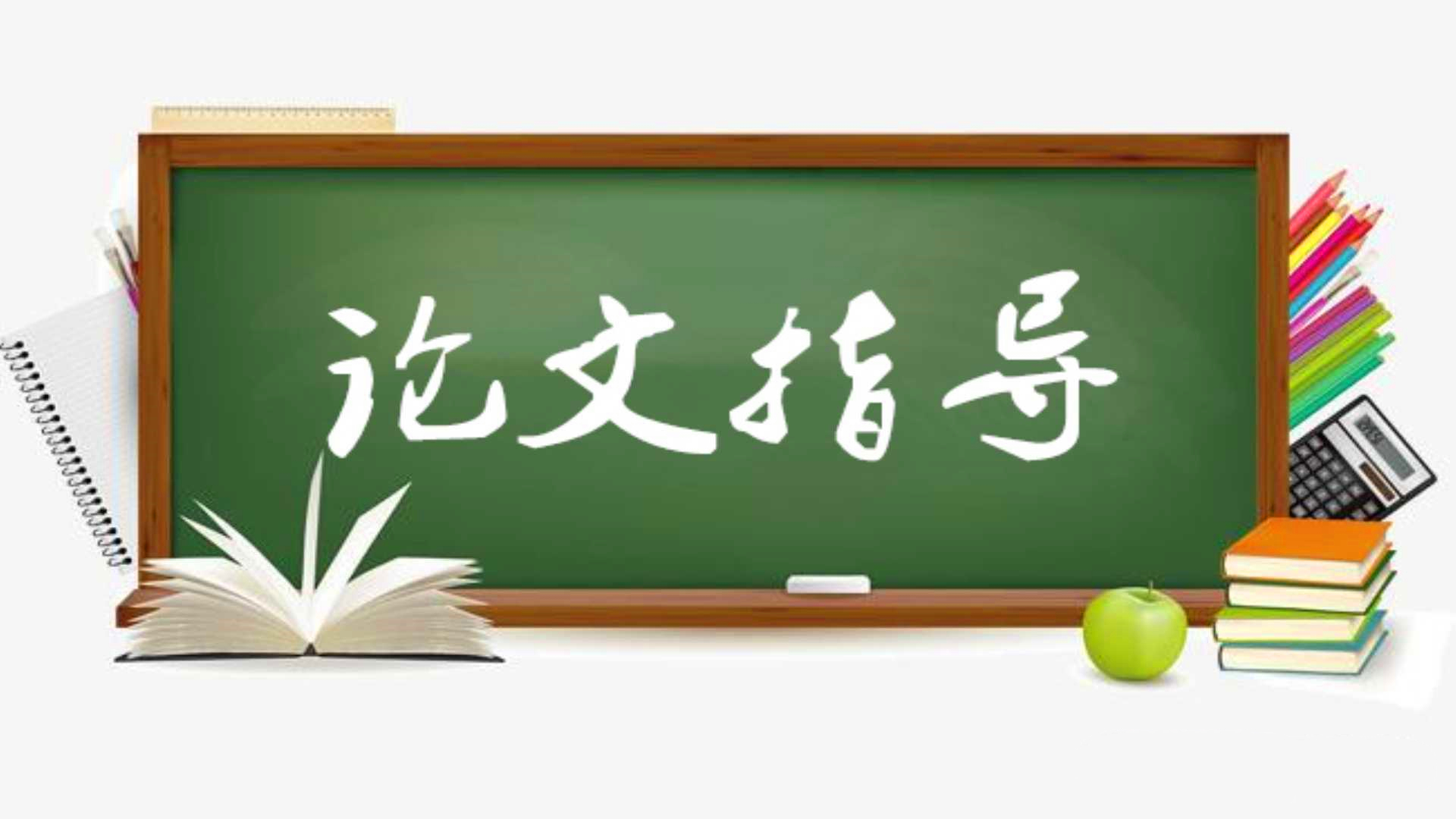
作為師范院校的一名教師,筆者從事十幾年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一直感到非常困惑和尷尬。一直感覺到自己很多時候有“誤人子弟”之嫌,原因之一就是我們教出去的學生,在無其他參考資料和教參的前提下,沒有能力分析和欣賞一篇中小學語文課文,寫不出一篇像樣點的文章或作文,甚至連基本的假條和申請都經常錯漏百出,確實感到悲哀和無奈。同時,對自己的工作意義和方法也產生了懷疑和疑慮。如果把責任推到學生和環境的身上,這未免有點草率和推卸責任之嫌,畢竟教學相長,教師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學生方面來說,我們也會經常聽到他們在說,大學學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在實際的教學工作中根本用不上。這就形成了互相埋怨和指責的漩渦當中,抓不住問題的核心而隔靴搔癢,使問題得不到根本的溝通和解決。進而中小學也在抱怨現在的大學畢業生綜合素質差,實際工作能力差,今非昔比,從而對我們師范院校的學生不認可,甚至排斥和反感。基于這些困惑和矛盾,根據自己的教學實踐和經驗,提出一些想法跟同行交流,以便自己更好地做好一名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師,不辜負學生、家長和社會對我們的期望,做到心安。
一、師范院校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的現狀
(一)課時壓縮,時間不夠
“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現代文學、中國當代文學)是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專業必修課,開的課時在整個“厚古薄今”的大環境下,課時越來越少。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北京大學溫儒敏先生感嘆:“北大目前中國現代文學課就只剩下72課時加上當代文學52課時,共124課時,各講一個學期,約等于過去的一半。”這一現象可能在其他院校也同樣存在,甚至更嚴重。就拿筆者所在的凱里學院開課情況來看,中國現當代文學總學時為80學時,中國現代文學史48學時,在第五學期開設,中國當代文學史32學時,在第六學期開設。而在2010年以前,中國現代文學史是72學時,中國當代文學史是54學時。在這樣少的課時里,要想像其他綜合性大學那樣面面俱到的講解中國現當代文學顯然不現實。那么我們怎么能在有限的課時里,講一些基本的、實用的內容呢?這是我們做教師的必須思考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如何能在有限的課時里,針對“師范”院校的學生以后出去是做中小學語文教師這一點,進行有針對性的教學。而現實的情況是,老師們還是按部就班地按原來的教學計劃,進行蜻蜓點水式的眉毛胡子一把抓地教學,而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和針對性的設計。
(二)教材統編,沒有針對性
?慕灘牡難∮每矗?很多大學選用的都是規劃教材,如:朱棟霖、丁帆、朱曉進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2013,上下冊),高等教育出版社,這本教材是“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著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洪子誠著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這兩本教材都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規劃教材”。我們學校這兩套教材都選用過,從2008年開始,全部選用北大出版的兩本教材。從總體上來看這兩本教材的學術水平確實能代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水平和研究狀況,都是出自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的權威專家學者之手,但這并不意味著這適合做教材。溫儒敏說:“這2本教材對一般低年級大學生來說,可能深了一點,也不適合那種照本宣科的講授,但有較多的空間可提供教師發揮,也能激發學生探究的興趣,所以出版后還是很受歡迎的,被很多大學采用。”教材對教學來講雖然不具有決定性作用,但對于我們這些普通二本師范院校很多時候教材的引領作用不可低估。從使用的效果來看,顯然針對性不強,學生也覺得看不懂教材,更沒有體現示范性,只是彰顯了學術性。另外這套教材對新的作品、作家涉獵較少,使學生不能了解當代文學的全貌,只是掌握了一些盲人摸象式的知識,不能窺見現當代文學的整體,而中小學語文教材卻經常涉及新的作家和作品。
(三)教學內容與中學小學語文課文脫節
其實大學的教學教材不是主要的問題,畢竟大學教學總體上來說是開放的、自由的,沒有那么多的限制和束縛,也沒有太多的統一考試來限制大學教學。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更應該發揮我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培養合格的人才。作為師范院校的學生來說,學生畢業就業去向85%以上都是從事教學工作。中小學語文教材選用的課文我們涉獵少,甚至根本就沒有。“在學科領域,師范教育特色的泯滅,突出地表現在中國現當代文學教材與中學語文教科書內容錯位。大學教材的編寫者很少考慮甚至完全漠視中學語文教學的實際狀況及未來發展方向的需求,中學語文教材里所選的作品在大學教材里偶爾有反映,難得一見。”“而遺憾的是,在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也包括其他文學課)的課堂上,教師一般仍沿襲著作家生平思想、作品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三個板塊’的教學模式,其著眼點主要在于提高學生的人文素質和文學是意識。對語文的‘工具性’訓練掉以輕心。而中學的語文教學在側重于字、詞、修辭手法、藝術風格的講授,即重視語言――文字――文章的‘工具性’教育”而這樣來思考師范院校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的從業者較少,致使我們的教學沒有做到有的放矢,致使學生畢業后“英雄無用武之地”。
(四)理論講授過多,作品分析較少
據筆者的了解很多大學在教授中國現代當文學的時候都是以文學思潮、文學史、文藝運動為主,體現文學史的地位,而忽視具體現代當文學作品的細讀和講解。當然在一些重點大學他們也在嘗試另外開設一門“現當代文學作品研究”來彌補其不足,而在一般的師范院校由于課時的限制和培養方案(應用型人才)限制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致使我們的學生畢業后不會分析和欣賞具體的文學作品,這種現象已經滲透到研究生階段,很多研究生畢業都還不具備解讀具體現當代作品的能力。陳思和先生曾說:“當輕視文本閱讀的治學態度漸漸地成了一種風氣,問題就有些嚴重起來。我這樣說,當然是有感而發――我每年主持研究生入學考試的時候,都會發現一些相同的現象:許多考生對幾本流行的文學史著作準備得相當充分,對一些流行的學術話題和讀物也相當熟悉,但是當你抽樣地選些文學作品作為問題的話,立刻就會發現破綻,他們對文學作品的閱讀量不僅相當少,而且幾乎不具備解讀作品的能力。曾有一位考生誠實地告訴我:他的導師對他說,做學問就要建立起一個自己的理論框架,然后把符合框架的作品往里面填。我聽了當時就告訴他,如果你學習現代文學史沒有成百成千地閱讀作品,沒有對現代文學史上的名著融會貫通,如數家珍,那么所謂的文學史理論體系都是別人的,而與你無關,你將永遠被關在這一專業的門檻之外,不會產生真正的獨立見解和自己的學術觀點。”作為一般院校的本科生,教師有必要對他們進行作品閱讀的引導,否則學生永遠都會被堵在文學門檻的外面,成為文學的門外漢。
(五)填鴨式教學,學生被動學習
大學很多教師不注重教學方法的研究和思考,只注重自己的學術研究,很多教師只管完成學校規定的教學任務,因為現行大學對教師的評價機制,重科研,輕教學,至于學生的反映,他們并不在乎。其實很多大學生對大學的課堂教?w不滿,但為了能夠順利拿到畢業證,他們只得忍氣吞聲,因為一旦得罪了老師就有課能掛科。作為現當代文學的教學也難逃大學教學的怪圈,沒有體現“以學生為主體,以教師為主導”的教學理念,沒有充分發揮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所以學習效果不理想。
二、改革措施和途徑
(一)教材編寫與中小學語文教科書銜接
高校教學雖然相對比較自由,對內容的要求不是那么嚴格,但教材的地位也不可忽視,尤其是在現在各種文化力量的博弈中,教材還是起到一定的引領和引導的作用。中學語文教學在不停的變化,作為師范院校應該引起高度重視。“2005年3月2日《新京報》報道――金庸《天龍八部》入選高中課本引發大辯論:在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語文讀本(必修)里,人民教育出版社首次選入了金庸的《天龍八部》片段,將其排在第六課,同時還選入了王度廬的《臥虎藏龍》片段,排在第五課,兩者合成一個單元――‘神奇武俠’。此讀本于2004年11月第一次出版,并向全國發行”而我們的現當代文學對武俠基本不講,我們選用的教材也沒有涉及這方面的內容。“高等師范院校的教材與綜合性大學應有所區別,這種不同就在于要突出其固有的師范特質。”“教材編寫者不僅應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研究專家,也應該是熟悉中學教育的里手行家,或者在編寫人員中吸收一定量的有研究能力的在職中學教師參加,使大學教材和中學教科書機密銜接起來,上下貫通,學以致用。”我們的做法是教材還是上述北大出版的兩本,對于里面的內容我們根據學生實際和中小學語文的現狀適當進行增減,沒有照本宣科,同時對中小學語文教科書新增加的涉及現當代文學的文章一定要分析。根據中小學語文教材對魯迅作品的減少,《魯迅研究》這門專業選修課被刪除,我們還開設了《現當代作家作品研究》、《新時期小說研究》、《現當代文學專題研究》等專業選修課輔助教學,并編有相關的教參或資料,供學生參考。同時,我們正在籌劃一門專業選修課《中小學語文中的現當代文學》,以適應中小學語文教科書的變化。
(二)明確培養目標,體現師范性
“師范”據《現代漢語詞典》解釋:師范,是師范學校的簡稱,師范學校,是指專門培養師資的學校。明確我們的培養目標――中小學師資,我們的學生出去要做教師即教書,以此為軸心展開我們的教學工作,只有目標明確了,我們才可以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在20世紀末的語文教育大討論時中學語文教師認為:許多批判者用過偏過高的標準要求基礎教育階段的中學語文教學,批判多限于‘文學’一隅,要求以大學為準,但倘若論者能俯視全國數千萬中小學生的實際情況,大致了解‘中學語文教學大綱’便不至于發此宏論。”因為中學語文教育(教學)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有機統一,這一點大學教師和學者又熟視無睹,所以我們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教學當中應該多注重工具性的滲透。在宏觀地講解的同時注重字、詞、修辭、藝術風格內容的穿插,是師范學生能夠單獨的去闡釋一篇文章,適應中小學語文教學的設計和需要。就像上述我們分析的那樣,不要像其他綜合性大學那樣,按照傳統的幾塊:文學思潮、作家生平、思想內容、藝術成就等去教授現當代文學,而是,以中小學語文教材選文為基點,從點到面的擴散開去,輻射整個現當代文學。這樣可能就有人認為,那么我們的現當代文學的教學,就沒有自己的體系了?當然不是,只是我們應該淡化“史”的線索,突出文本細讀和具體作品的分析。由于課時的限制,至于作家生平、創作情況可以讓學生自學,老師檢查自學效果的方式進行。筆者的做法是,把班級分成若干小組,每個小組完成一個或幾個作家基本情況的收集整理,并請代表發言,之后教師補充。這樣就節約了很多時間,也提高了學生參與的積極性,畢竟有任務,他不不去查資料。這樣一來,教師的功課就多些,自己得熟悉中小學語文教學基本情況,還得布置有一定水平的作業,并指導。現在的情況是由于大學評價機制的問題,很多教師只是完成教學任務,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也許會有同行認為,至于具體作品分析師范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不是還有“中學語文教學法”嗎?沒錯,但“中學語文教學法”它是針對整個中學語文教學而言的(不僅有文學還有語言和文化等),沒有板塊的針對性,且中學語文教學法,又完全立足于中學語文來闡述,對大學的文學教學現狀沒有涉及,這就使二者脫節,理想的狀態是大學文學教學與中學語文教學法有機結合,互相照應。
(三)改革教學方法,調動學生學習主動性
教學方法是實現教學目標的手段,因為大學教育評價機制的寬松性,大學教師對教學方法相對于中小學教師來說是比較陳舊和死板的,正因為此,很多大學生對大學老師的教學能力評價不高。在我看來,作為師范院校的教師更應該注重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因為我們應該給學生樹立好榜樣,我們應該是“老師的老師”“老師中的老師”。如果自己的教學方法陳舊或不當,我們又如何去指導學生試講和實習呢?即使指導了又有什么效果呢?我們應該用最簡潔的方式,深入淺出地傳授知識,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大學教師,尤其是文科教師存在的合法性就應該受到質疑,因為教材和參考書籍學生可以自己看看和研讀。作為現當代文學來說,有些知識、作家和作品不能囿于教材和時期,而應打破常規使學生更易于掌握和理解。就像謝廷秋老師做的那樣:“因此,筆者的改革思路是,改原來的文學史帶作家的講授為作家帶文學史的講授法,重點放在文學的主體上。講清楚不同層次作家的價值取向,藝術風格如何匯成主流在這個層面上發揮作用,在某一個階段的運動軌跡。講授可以多采用比較的方法,除了不同層次的作家比較而外,有的跨越解放前后的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冰心、曹禺、巴金等,均在一個層次上講完,不必再像過去分別在兩門課程中都要講到,而且可以將他們不同階段的創作加以比較,用20世紀的宏闊視野來觀照他們的創作,從中看出新文學發展的曲折性,加深對圓形結構的理解。”也就是說教材和內容是死的,教學方法是活的,我們可以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和教師自身的情況選擇相應的教學方法,做到因材施教,因人而異。筆者除了采用謝廷秋老師講的方法外,還采取另外一些方法。在開學之初就把班級分成若干小組,每組分派一些內容,這些內容需要他們去查資料,準備好之后,他們自己選代表上臺講解。這樣既提高了他們學習現當代文學的積極性和節約了課時,同時還鍛煉了他們的教學實際操作能力。其次,就是講授與討論并舉。如講曹禺這一章,我先布置學生準備,讓他們自由發言,自由討論,筆者做旁觀者適當點撥,再輔助以作業。再次是征求學生的意見哪些地方該講,哪些地方該放,并說明理由。這樣我們就不囿于教材內容,擴寬了現當代文學的界限。總之,在教學方法上,我相信“教學有法,但無定法,貴在得法”,作為師范院校的教師,教學的最終結果是“教師教得好不好,學生會不會見分曉”。
(四)增加課時,完善培養方案
充足的課時是提高教學質量的基本保障。凱里學院漢語言文學師范專業對培養方案每四年進行一次修訂,根據教學效果和教學實際需求,對專業基礎課進行適當的調整。調整主要涉及課程安排的時間和課時。雖然適當增加了相應的課時,但還是不能滿足教學需求,所以我們增開了《現當代作家作品研究》、《新時期小說研究》、《現當代文學專題研究》、《中小學語文中的現當代文學》等專業選修課程來彌補課時的不足,進一步完善“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的立體結構,力爭培養合格的中小學語文教師。
總而言之,作為師范院校現當代文學教學在完成基本教學目標的同時,一定要體現師范性,不能跟其他綜合性大學的現當代文學教學相比,我們一定要與中小學語文教學銜接,做到有的放矢,因材施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