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讀老舍《茶館》的語言之恨、傳統之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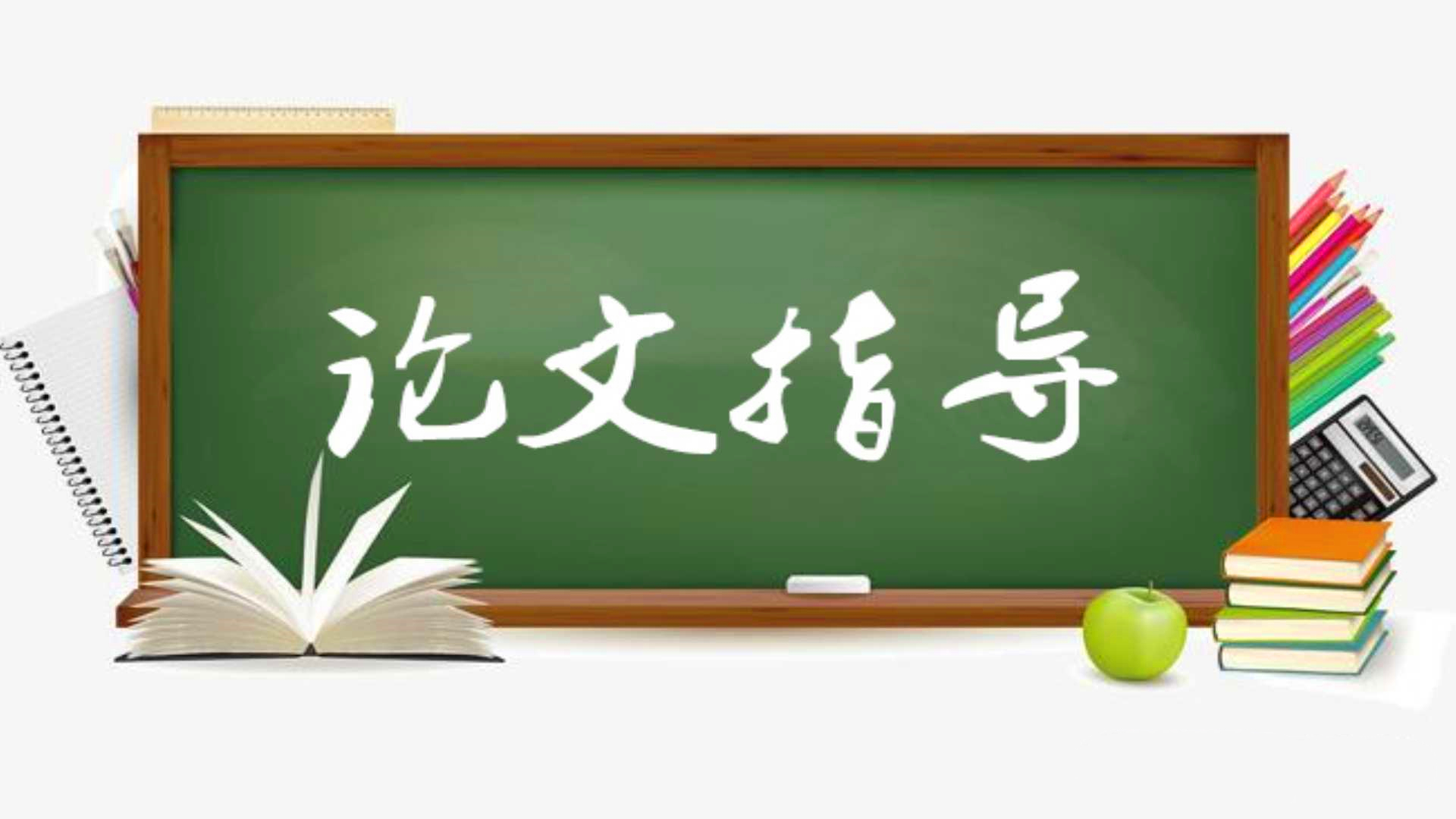
《茶館》可謂是老舍戲劇作品中的翹楚,劇中的三幕,一幕寫一時代,每一幕都敲響了一個時代的喪鐘。老舍先生以獨特的構思,以茶館為舞臺,著眼于小人物的生活命運,揭示了舊中國的黑暗。細讀《茶館》,我們無一不為之動容甚至涕零。下面,筆者就從詼諧語言、沒落茶館兩個角度進行品味。
一、詼諧語言,品不完的徹骨之恨
老舍先生用純熟的語言技巧,讓劇中人物的語言于詼諧中泛涌淚花。很多人物的語言表面看似滑稽可笑,但是在笑聲逝去之后,留給讀者的是更多的沉思與憤恨。
例如,常四爺見二德子在茶館“抖威風”,鄙棄其恃強凌弱,只可窩里斗狠,二德子卻全不要臉面言:“怎么著?我碰不了洋人,還碰不了你嗎?”這是何等的“威風”啊,在面對自己毫無寸鐵的同胞時,把土匪流氓“氣質”展現得淋漓盡致。在洋人的淫威之下,俯首稱狗,吮血國人,無絲毫憐憫之心,在平民與學生面前大展身手,威風凜然,勇當帝國主義侵略中華民族的“急先鋒”。常四爺看到劉麻子在炫耀自己又細又純、地道英國造的鼻煙壺時,悲嘆大清國的真金白銀涌流國外,而劉麻子卻無比自豪,“咱大清國有的是金山銀山,永遠花不完!”清末,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讓整個大清國滿目瘡痍,整個民族處于水生火熱之中,百姓枉死,家園遭毀。但是,這僅僅是個開端,戰爭的后續帶來的是更多的經濟侵略和文化侵略。而作為國人的一份子——劉麻子,卻仍然處于一種沒落卻無意識的自我優越之中。
在紛繁的亂世中,唐鐵嘴的相命生意卻越來越好。正如他所言,“這年月,誰活著誰死都碰運氣,怎能不多算算命、相相面呢?”詼諧的語言中,透露出百姓的顛沛流離之苦,命在旦夕之悲,而唐鐵嘴卻利用百姓禍難大發橫財。八國聯軍侵入北京之際,逃竄的百姓在洋人的槍炮聲中倒在血泊里,而此時的劉麻子卻搶奪一個個無家可歸的孩子,何其痛也!唐鐵嘴很自豪地向王利發說道,自己已經不再抽大煙了,改抽白面了,“兩個強國侍候著我一個人,這點福氣還小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之狠、之無恥有目共睹,鴉片的輸入與肆虐,中華民族被推至于懸崖邊緣。看似滑稽的語言正體現民族的悲哀,而唐鐵嘴之類無任何覺悟之心,甘于被奴役、被毒害。
二、沒落茶館,訴不盡的傳統之殤
茶館可謂中國古典文化的縮影,是一種特有的文化現象。清代茶館遍布城鄉,其數量也是歷史上少見的。北京有名的茶館就高達30多個。生活在北京城的老舍與茶館有著緊密的聯系。老舍出生的小楊家胡同口里就有一個茶館,老舍的父親舒永壽在回家的路上經常經過“天泰軒”茶館,他曾是這里的常客。在這樣一種傳統生活方式的影響下,老舍對茶館自然有一份獨特的感情。“除了讀書以外,慶春就是愛去個小茶館聽聽說書的,上天橋看個‘噌兒戲’“他跑熟了北京城的大小茶館,聽了、看了一肚子的典故和故事”。
中國人上茶館,到明清時期不僅是日常生活的需要,更主要的是精神生活的需要。品一壺香茗,談一種人生,上茶館已經成為一些人的生活方式,成為特定身份群體的文化符號。就像老舍在《茶館》中第一幕所言,茶客來到茶館里不僅是吃點“簡單的點心與菜飯”,很多人“遛夠了畫眉、黃鳥之后”,聚集茶館“歇歇腳、喝喝茶”,“商議事情”,談論一些“荒唐的新聞”“奇怪的意見”,聽聽“某京戲演員新近創造了什么腔兒”,忘記生活的艱辛、忘記情緒的紛雜,靜享這片刻的悠閑。
然而,晚清中國茶館的環境變得污濁起來,烏七八糟。打架斗毆、欺軟怕硬的流氓,販賣人口的、拉纖扯皮的潑皮,鴉片、白面等污濁之物也時常出現在茶館。到了民國初年,茶館的生意更加慘淡,一種純粹的、古典的傳統文化正在逐漸消亡。一方面,在帝國主義的指使下,國內戰亂不斷,民不聊生,百姓無閑心去茶館;另一方面,西方生活習俗也沖擊了茶館的生意,咖啡館、西餐館、酒吧等在各個公園、街頭巷尾出現。《茶館》中的王利發為了避免淘汰,對“裕泰”茶館進行了改良,將原有的長桌、長凳換成蓋著淺綠桌布的“小桌與藤椅”,撤去墻上的“醉八仙”大畫,連財神龕,代以外國香煙公司的廣告畫。然而,茶館原有的清新、雅致、具有大眾化文化氣息的特點逐漸減弱,甚至消失。到抗戰勝利后,在國民黨特務和美國兵的橫行下,裕泰茶館更加不如以前體面了,在各種勢力的摧殘之下終于關門大吉了。
綜上所述,《茶館》的成功并不是偶然,其熔鑄了作者的真實經歷和復雜情感。對往事的嘆惋,對“茶館”文化的憑吊,對外來侵略者的痛恨,對腐朽清王朝的無奈……種種情感交雜,或溢于既詼諧又充滿諷刺的語言,或露于人物的行為動作,也正是這些存在給了讀者無盡的思索,也讓《茶館》成為一部經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