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歌小說研究綜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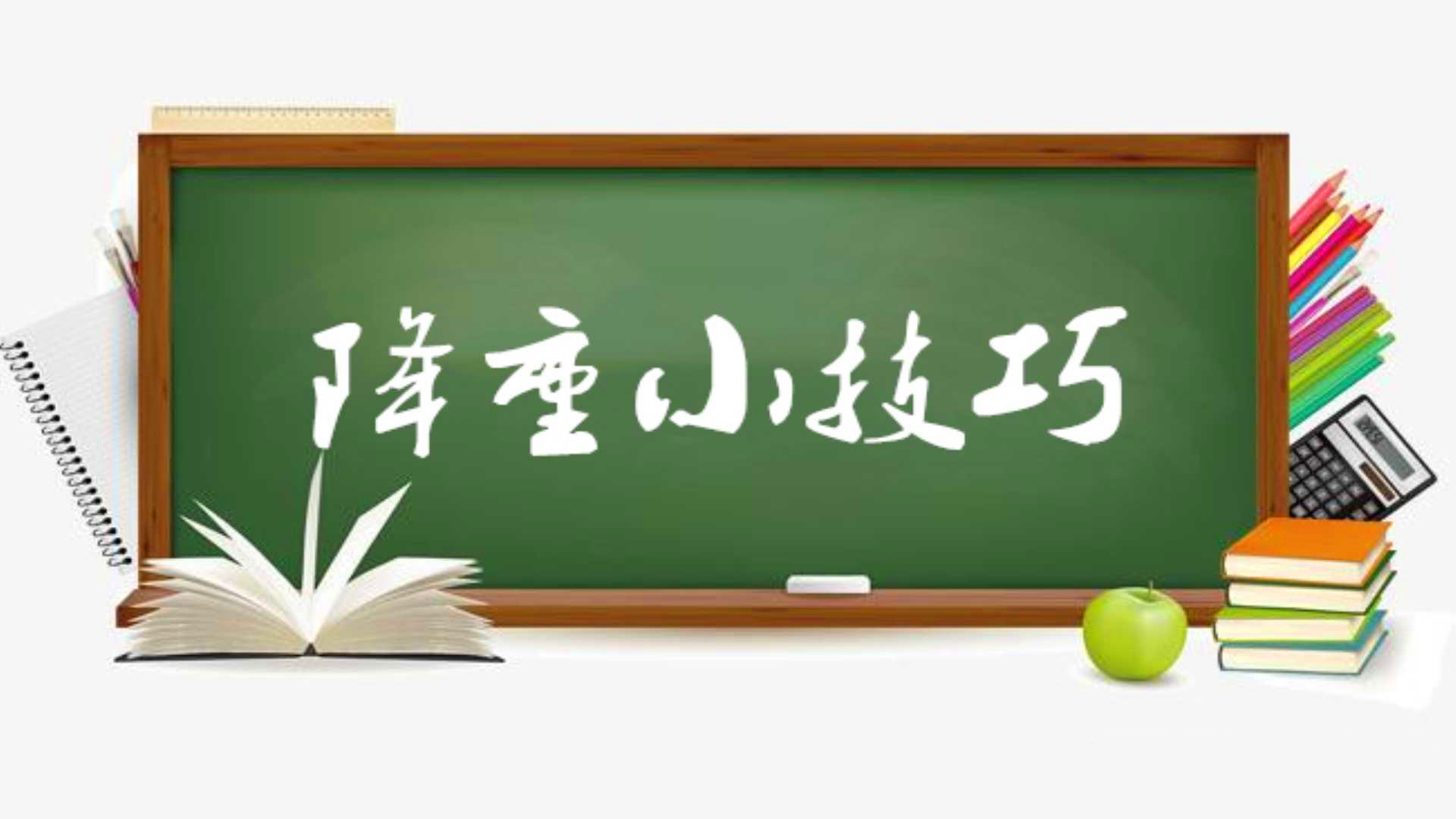
顏歌,真名戴月行,是“80”后最具先鋒姿態的實力作家,1984年出生于四川。顏歌從2002年開始創作,在《人民文學》、《萌芽》等刊物上發表小說,著有長篇《我們家》、《聲音樂團》、《異獸志》、《五月女王》、《關河》,中短篇小說《良辰》、《桃樂鎮的春天》、《蜂王》、《在人間》等。曾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潛力新人、巴金文學獎長篇小說獎、中國青年作家小說十佳等。她的作品被翻譯成各種語言流傳到國外,她也是四川省作協的簽約作家。
21世紀初,消費主義的洪流將“80”后作家推向了文壇。市場出現了大量的暢銷文學作品,一大部分“80”后作家的作品被冠以“青春”、“傷感”、“疼痛”等的標簽。但是在當今娛樂化、商業化、標簽化的文學語境中,也有努力探索尋求自己獨特的文學道路的作家,他們試圖打破這種商業化、標簽化的束縛,創造出一個更純潔的文學世界。顏歌便是其中的代表,從《良辰》開始,出生于四川的顏歌,便將眼光投之于自己的家鄉——郫縣。《五月女王》、《聲音樂團》、《平樂鎮傷心故事集》、《我們家》等,顏歌為自己的文學建構了一個屬于自己的地域——平樂鎮。作為年輕作家,顏歌一直用自己獨特的筆觸反抗世人對“80”后作家籠統的評價。顏歌屬于成長期的作家,所以對其創作風格不能有個定論,從文學界對顏歌的研究來看,文獻資料相對稀少,學術論文對其研究也是被囊括在“80”后作家里進行籠統的研究。將其與其他作家放在一起比較的碩士論文也只有5篇,期刊論文40余篇,通過對碩博論文和期刊論文的閱讀梳理,可以發現學術界對顏歌的研究主要分為整體的宏觀把握,經典作品的微觀分析和與相關作家的整體研析三個方面。本文將主要從這三個方面出發,對顏歌作品的研究成果進行歸納、梳理,從而達到對該作家的研究狀況有一個整體的把握。
一.顏歌作品的整體把握
從2002年創作至今,顏歌的所有小說作品可以大體被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對現實的奇幻探索,二是對人性的挖掘與探視。這些作品中對典型人物的塑造、對意味深長的主題的追求和川味的語言特色等等,都包含了顏歌自我情感和體驗的表達。她說:“歸根結底,小說家的‘現實’只是他內心世界的投影。所謂魔幻的或者在我的例子里是‘鄉土的’,這些都只是作者內心世界的反映。”顏歌的小說總能在無形中讀出不同于她年齡的成熟,這樣獨特的閱讀體驗使得顏歌在80后作家中脫穎而出,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1)青春主題的依戀與擯棄
顏歌早期靠著才氣與勇氣所寫就的《十七月葬》和《關河》等作品,那些作品的名稱是《錦瑟》、《天涯》、《絕塵》、《桃源歸》等等,僅從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年輕的顏歌對古典雅致語言的熱愛和對歷史題材的崇尚,伴隨著一種帶著一代人去體會古典語言的使命感,她避開了現實,在歷史中撿拾故事,把自己對于青春的孤獨、對愛的幻想、對生活的困惑填充進去,她善用華美的辭藻,善用充滿回環一位的短句,善于營造唯美凄麗的意境,這些故事是十六、七歲的顏歌的青春書寫,充滿她的個人特色,她用想象和奇幻包裝,但其實這些作品的題材包含著青春少女的綺麗思緒、青春成長的淡淡孤獨,是不脫青春文學的窠臼的。對顏歌青春題材小說的研究不多,陳思廣和孫婷婷的《在更深廣的視野中——談顏歌小說中的青春成長書寫》中,從顏歌青春成長書寫的背景和姿態、所處的復雜關系圖以及青春成長書寫的意義這三個板塊出發,對顏歌青春小說的特點和與眾不同之處進行研析。但顏歌不喜歡80后青春寫作的標簽,不愿意歸類到青春寫作作家當中去,不愿意自己的作品淪為文化商業現象,因此她也在不斷改變自己的文風,慢慢地走向成熟。小說《五月女王》中,加重了現實的成分,它將故事本身的敘述放在了首位上。而且在這部小說中開始建構她地理版圖上的另一個地方:平樂鎮。2012顏歌的《我們家》這部小說標志著顏歌從青春文學向嚴肅文學的大轉變。到2015年,她熟練地使用著四川方言在她所建構的平樂鎮上暢行,這個時候,故事背景完全找不到奇幻和青春的影子,我們所能看到的是西門上春娟豆瓣廠,西門城墻邊花椒店,出了南城的幺五一條街,七仙橋的肥腸粉,字里行間散發著辣椒油、豆瓣醬的香氣,這些地理節點牽連架構除了整一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學場域,與“青春”二字仿佛成為一對反義詞。這些創作是告別青春寫作的故作殘酷之后的人生冷暖,是告別青春寫作的虛渺幻想之后的真切體悟。對顏歌的創作風格改變的研究也不多,有王濤的《試論顏歌近期小說創作中的轉向》中,從顏歌的早期作品出發,對其“神話”敘事中的成長傷感、“志怪摹寫”中的人性探索進行研究,觀察其寫作技巧的日益成熟。
(2)敘事風格與語言的分析
顏歌小說有著別具魅力的綺麗想象和精致細膩的古典語言,藝術的最卓之處就是她對方言熟練地駕馭,正因為如此,對顏歌的“鄉愁”、“地域性”、“川味”的研究頗多。不過,因為顏歌創作始于十六、七歲,所以風格沒有定型,而是在逐漸走向成熟。許寶丹在《貼地飛行的文學轉身——論顏歌“平樂鎮”小說創作》中認為,顏歌前期的小說是城市魔幻現實主義,后期創作的《我們家》和《平樂鎮傷心故事集》則是現實主義的,形式和手法上有一定的先鋒性;賈蔓和許林的《顏歌:“80”后的出走者》則認為顏歌的前期作品有同時代作家描寫殘酷青春的通病,但在其不斷的創作實踐和多種題材的嘗試之后,則是以鄉土為立足點,愈發的樸實俗白,貼近日常生活。
二.顏歌經典作品的分析
顏歌雖然從2002年開始創作,但作品數量相對可觀,更有《我們家》、《聲音樂團》、《五月女王》、《異獸志》等經典長篇小說。顏歌對社會以及文學的探索和理解經歷著不斷的變化。無論是中短篇還是長篇,無論是奇思妙想的奇幻故事還是都市生活的展現,對她的小說研究從外在的遣詞用句到內在的寫作旗幟都可以作為文學研究的挖掘對象,對其小說特點的論證有利于豐富當代作家長廊的人物類型,開拓小說的多樣化寫作,也有利于小說特色化寫作的探索。
(1)短篇小說個案研究
顏歌的短篇小說創作頗豐,更是出版了《平樂鎮傷心故事集》、《良辰》、《十七月葬》等中短篇小說集,對于短篇小說的研究意義很大,但是對于顏歌的短篇小說研究并不多,至今的研究只有對《平樂鎮傷心故事集》這部短篇小說集的一篇。《平樂鎮傷心故事集》是2015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作者在這部小說集中通過普通話與方言夾雜的方式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幅融合日常與奇幻的川西小鎮的市民生活場景。就是鐘娜的《顏歌造字:<平樂鎮傷心故事集>》。該篇從顏歌的語言使用出發,分析顏歌方言使用的特色和方言的使用在小說中所體現出的川味。
(2)長篇小說的個案解讀
顏歌至今的長篇小說主要有《我們家》、《聲音樂團》、《五月女王》、《關河》、《異獸志》五篇,對其長篇的單篇研究文章月約有10篇,從不同的角度解讀作品的人物形象、主題思想和敘事結構。
對《聲音樂團》的研究只有兩篇,一篇是李暢的《一部恢宏的文藝交響樂——顏歌<聲音樂團簡論>》,從敘事結構、主題思想和人物形象出發,體現出顏歌既長于敘事有長于場景描寫的語言特點,結合奇幻因素和地域描寫,分析顏歌的創作特點。一篇是宋騏遠的《<聲音樂團>的敘述特色》,從敘事的角度出發,分析顏歌《聲音樂團》的敘述特色,并分析了帶有先鋒性特色的顏歌小說在敘事方面的缺點。
對《異獸志》的單篇研究只有一篇,是朱婧的《顏歌<異獸志>與新怪異小說》,此篇以寫作特色出發,分析其對新志怪小說的承襲和創新,解讀顏歌的創作風格。
對《五月女王》的單篇研究目前還未出現。對《我們家》的單篇研究相對較多,分別是崔劍劍的《<我們家>:80后文學的第四個方向》,從方言寫作和喜劇手法出發分析顏歌的創作手法;劉祺杭《<我們家>復調敘述視角的建構》,從敘事學出發分析顏歌寫作技巧的成熟;廖海杰《川味的輕逸與密集的私情——讀顏歌<我們家>》和伍月《論顏歌<我們家>中的“川味”》則都是從地域性出發,分析生長環境對顏歌創作的影響以及顏歌創作中的地域特色。
三.顏歌小說整體納入與比較研究
顏歌是20世紀80年代出生在四川的作家,從她出生的年代和地域來看,其作品就不可避免的會被研究者所關注。“80”后作家生長的年代是一個經濟迅速發展、網絡大肆流行的時代,他們的寫作不可避免的被打上了消費時代的烙印。
(1)地域文化影響下的研究
在顏歌的小說中,我們經常能看到四川這個地域空間的存在,顏歌作為土生土長的四川人,對自己的家鄉有著不一樣的情感,就像蘇州之于范小青、東北高密之于莫言、北京之于張恨水、湘西之于沈從文。顏歌則擁有永安平樂鎮,范小青曾說:“即使沒有福克納以及其他什么名人名言,我也會繼續傻乎乎地站在我的這塊比郵票更狹窄的地方折騰下去,寫它的過去,更寫它的現在,為它痛苦,為他快活,因為我生活在這里,我的根在這里,更因為我筆耕的這個時代,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大有寫頭的時代。”顏歌則是以四川為原型,寫它的過去、現在甚至奇思妙想的故事。顏歌說:“平樂鎮就是我的理想國、烏托邦。平樂鎮的一切,寫起來的時候都讓我飽含著淚水。”
四川,曾在不同作家筆下被無數次的書寫過,如李劼人、沙汀、艾蕪等,顏歌憑借其獨特的想象力和語言的成功運用,也成功激起了研究者的興趣。王晴飛在《顏歌的腔調與鄉愁》里認為:“小說的敘述語言主要是四川方言,評論者多注意到方言的生動和地方風味,而實際上方言在這部小說中一個重要的功能是寄托鄉愁。”從《良辰》開始到《我們家》,顏歌的作品無論是長篇短篇,敘事風格雖然多變,但方言的幾乎在每部作品里都有運用。受四川文化的影響,顏歌的多數作品都是以四川為背景,所以也被學術界納入四川作家群來研究。但相關論文只有2篇,有游翠萍和向榮的《現代性話語影響下的四川鄉土敘事與女性形象》,對四川作家的四川鄉土敘事進行分期分析,歸納出他們的共同特點,分析比較他們在文本主題、敘述方式、藝術風格等方面的不同。還有何勝莉的《大眾寫作vs嚴肅寫作——四川80后作家文學態勢芻議》,中對80后的四川作家進行了比較分析,將他們劃分為大眾寫作和嚴肅寫作兩個陣營,分析他們在市場上不同的寫作方向。
(2)80后背景下的比較分析
今天的“80”后寫作者,面對的是這樣一種事實:“他們年輕,具有充沛的熱情與精力,龐雜多元的想象力,后勁兇猛的創造力,他們的書本正一本一本的出版,擠滿各大書店的暢銷書柜。”花樣百出的寫作姿態和宣傳手段,使得他們不容爭議的占據著中國文壇的眼球中心,甚至引領著文化消費市場的方向。除此之外,由于新媒體、新時代、新文類的蓬勃發展,“80”后作家崛起,從2003年起,80后的作品開始占據文學消費市場的10%,在這個青少年文學斷層的社會成為絕大多數青少年成長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80后文學作為一種整體現象開始為世人所關注,成為文壇上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早期的“80”后文學以青春文學的態勢存在,備受爭議,游離在主流評論圈以外。但隨著80后文學群體創作的逐漸成熟,逐漸劃分為兩個陣營。一是面向大眾消費市場以商業寫作為主,以互聯網或圖書市場為主要渠道,以盈利為主要目的的大眾寫作。如郭敬明、韓寒、明曉溪、落落等。二是面對文學傳統,以嚴肅寫作為主,以傳統文學刊物作為陣地,漸漸融入主流文壇的嚴肅寫作。如張悅然、顏歌、小飯、孫頻等。顏歌作為在消費時代的洪流中逆流而上的純文學作家,也成為了研究的焦點,常常被放在“80后”作家這一群體中進行比較研究。
顏歌作為一名新生代作家,所以從一開始就不可避免的被放在80年代出生作家的群體中和消費時代的背景下進行研究。對顏歌該情況下碩博論文研究有4篇。有葛思思的《80后文學的青春散場——以顏歌的小說創作為中心》,分析了80后作家在主題、敘事策略和語言上的共同點以及不同之處,比較和分析80后作家創作的特點。祁春風的《自我認同視野下的“80”后青春敘事》認為:“顏歌代表了80后文化認同的另一種情況,他們在經歷了大城市、甚至國外的生活后,與后現代文化逆向而行,回歸民間文化、地方文化,講述起自己在故鄉小鎮的成長經驗,表現小鎮生活和文化”。與快速發展推進的迎合消費文化的作品截然不同。 還有王江梅的《80后小說中的鄉土書寫》從80后作家建構的文學空間出發,對80后作家在作品中建構的文學空間進行梳理,探究80后作家對傳統的回歸;喬宏智《80后長篇小說研究》,對多樣化的80后長篇小說敘事主題進行分析,劃分出成長主題、歷史主題、生存現實困境主題等,解讀其中多樣化的寫作風格。
四.研究中的缺憾
縱觀顏歌小說研究的相關資料,成果不是特別豐富,也存在著諸多不可忽視的問題。首先,顏歌小說中涉及到的人物很多,男女老少各色人等,但并無對其人物形象的單獨研究。其次,學術界對顏歌小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長篇小說如《我們家》和《五月女王》等,呈現扎堆研究,對于短篇小說的研究很少有人關注,即使有研究短篇小說的文章,也呈現集體性研究,將短篇小說作為研究其風格變化的論證,而且對于顏歌的研究多從地域、鄉土的角度分析,忽略了其前期創作的魔幻現實主義,缺少新穎性。最后,對顏歌的碩士論文研究現狀是都將其放在80后作家群體中進行比較研究。這些在顏歌作品研究中隱藏的小問題不容忽視,需要研究者們一步步解決。
顏歌是處在成長期和發展期的作家,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其小說的創作會有更加廣闊的背景,會為我們呈現出更具美麗和價值的文學作品,也相信未來對于顏歌的作家作品研究會越來越豐富。
參考文獻(略)
本文收集整理于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系客服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