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青年”張聞天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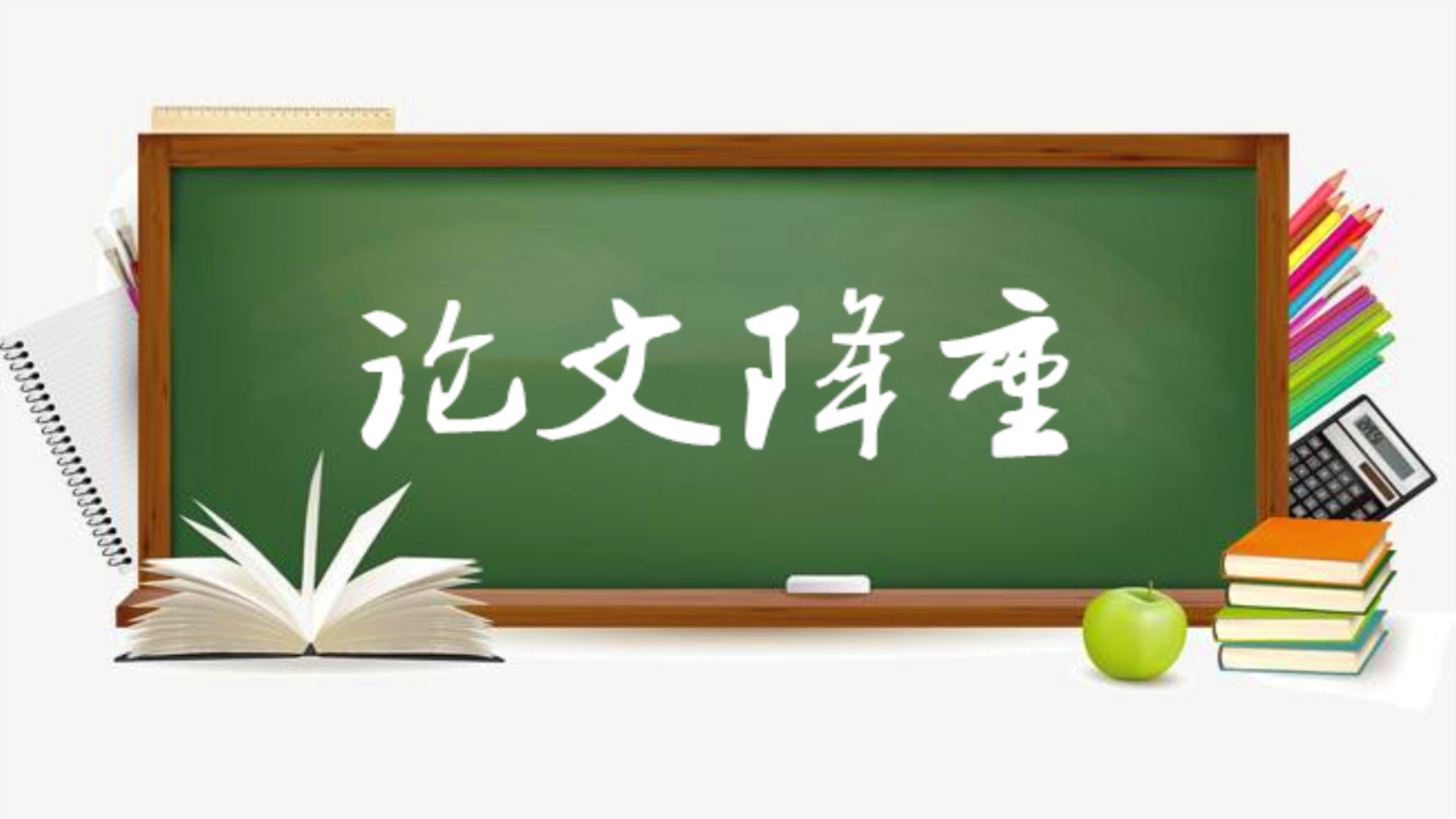
本文是一篇文學論文,筆者通過考察“文學青年”張聞天與“五四”時期其他思潮、流派的多樣聯系,揭示影響其文學心理的復雜因素,呈現其文學思想生成發展過程中的復雜沖突與糾葛,能夠有效窺見“五四”時期被“召喚”的新知識分子精神發展的一種軌跡。
第一章“河海”時期:“新青年”的最初覺醒
第一節河海工程專門學校的教育
自列強以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大門,外辱日深。為強國御辱、解民倒懸,仁人志士不斷探索著救國救民之道。眾人各抱其說,各行其是,積極尋求療救良方。五四前后,西方思想得到更加廣泛傳播,并與中國社會現實碰撞融合。一時各類救國思潮“百花齊放”,呈現出蓬勃之勢。發端于鴉片戰爭時期的“實業救國”思潮此時再次盛行。以張謇、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審視現實國情的基礎上,反思和總結歷史經驗,試圖通過振興實業的方式,挽民族于危亡。“救國為目前之急”已成為廣泛共識,然而,張謇認為,“軍事救國”“教育救國”等不同主張理應有“緩急之序”。“譬之樹然,教育猶花,海陸軍猶果也,而其根本則在實業。若騖其花與果之燦爛甘美而忘其本,不知花與過將何附而何自生。”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興實業之緊迫,“凡強國可以至此者,起源千條萬端,而悉歸于實業。”
文學論文怎么寫
“實業救國”思潮的流行極大地影響著當時的青年。據郭沫若回憶,“在我們的那個時代是鄙棄文學的時代,實業救國、科學救國的口號成為了一般智識階級的口頭禪。凡是稍微有點資質的人都有傾向于科學或實業的志愿……”,“二三十年前的青少年差不多每一個人都可以說是國家主義者。那時的口號是‘富國強兵’。稍有志趣的人,誰都想學些實際的學問來把國家強盛起來……”興實業以救國的理想,使時人對文學“有一種普遍的厭棄”。在這種潮流的影響下,郭沫若被“逼著出了鄉關”,到日本學習醫科,雖傾心于文藝,也只能“存心克服它”。后來記錄學生時代時,郭沫若再一次坦陳心志,“我在初,認真是想學一點醫,來作為對于國家社會的切實貢獻”,然而終究沒有學成,這被郭沫若引為憾事。郭沫若的好友成仿吾進修于東京大學兵器制造科,張資平學地質學,可見,“研究實際學問”成為當時青年的一種普遍志業選擇。
..............................
第二節“開導無知識”:革命的前提
“河海”在“五四”運動爆發后迅速成為南京地區的中堅力量,校長許肇南被推選為南京學界聯合會臨時主席,張聞天、沈澤民、丁繩武等學生也積極投身反帝愛國運動,成為南京學生聯合會的骨干。“六三”風波平息后,當局唯恐學潮再起,命令全國學校提前放假。張聞天、沈澤民并未離校,而是積極參與到《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的編輯工作中。
《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創辦于1919年6月23日,是“五四”期間南京地區的第一份進步刊物,由南高師國文科學生阮真擔任主編,張聞天同沈澤民、劉英士、董開章、丁繩武等人共同擔任編輯科科員。任職期間,張聞天積極撰文,現存的50號刊物中,有15號刊載了他的文章。需要注意的是,這時寫作于張聞天而言,并非“攏著一雙雪白的手,立在不受危險的地方,發幾句不關痛癢的議論”,而是一種與學生運動等同的重要的政治參與方式。張聞天認為,解決社會問題最要緊的是“鏟除士大夫階級”。“士大夫階級”如何鏟除?需要勞農界人共同起革命。而勞農界人現在“一點知識都沒有”,處于混沌蒙昧的狀態中,對自身處境無知無覺。這便需要“有知識的開導無知識”,然后大家一起干涉政治。張聞天的寫作即基于“開導無知識”,即啟蒙的目的。這里被反復強調的“知識”,并非科學知識,而是指政治“常識”。在張聞天發表在《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的文章中,國家、社會、國民、平等、自由、博愛、法律、道德等概念被反復闡釋。
............................
第二章青年的夢:新村、工讀與精神運動
第一節“民眾的力量”:社會觀念的覺醒
民初民主革命的成果與人們心中為之規劃的美好藍圖相去甚遠。有人真實記錄了這種心理落差:“自有清國變,改造共和,革命諸子創中國數千年未見之業,人民歡慶,皆曰吾國從此可由弱而轉強也。不意數載于茲,兵連禍結,百政莫舉,全國紛紜,內訌未已,外患加逼。”歷次政治運動的失敗,使知識分子對政治革命深感失望,“沉淪的現實”如何才能通向“理想的未來”,人們對此展開了新的思考,社會的觀念因此覺醒。“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大家于是覺得以政治去改造政治,是沒有用的;于是想到以社會的力量,去改革政治。大戰的影響,是以外力促醒社會的觀念;內亂的結果,是以內力促醒社會的觀念。……民眾既然發現了這個社會了!”
“社會”的發現基于對“國家”偶像的破壞。陳獨秀在《說國家》(1904年6月14日《安徽俗話報》第5期)中,指出了“國家”的三個要素,即一定的土地、一定的人民、一定的主權。此三者緊密聯系,共同建構了“國家”的概念,并且處于同等重要的位置,“缺少一樣,都不能算是一個國”。張聞天也以此三要素闡釋“國家”這一概念:“國家是有一定土地,有一定人民,有一定主權,缺少了一樣就不成其為國家。”與陳獨秀不同的是,張聞天格外強調了“主權”之于“國家”的重要意義,這與剛剛過去的外交風波不無關系。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二號發表了陳獨秀的《偶像破壞論》,“國家”作為“偶像”之一,也被納入破壞之列。這篇文章中陳獨秀再次談到“土地”與“人民”兩種要素,“一個國家,乃是一種或數種人民集合起來,占據一塊土地,假定的名稱”。“主權”似乎被忽略,但這并不是因為國家不再面臨“主權”危機,而是陳對政府的信任危機不斷加重。一國之中,制定刑法、征收關稅、修正軍備、辦理外交等種種國政都要倚仗“主權”,而行使“主權”的權力歸于國民政府,可見,對于政府的權威,陳獨秀當時是認可的。轉變發生在辛亥革命之后,尤其是1914年前后,袁世凱掀起的復古逆流,百政俱廢,人民生機斷絕,引得知識界人士相當憤慨,對政治的失望情緒不斷蔓延。
................................
第二節“青年的夢”:新村的美好藍圖
如果說在《“五七”后的經過及將來》與《中華民國平民注意》中張聞天試圖通過呼吁國家制度改革與新國民的創造使“一切問題迎刃而解”,《社會問題》中,張聞天完成了社會的發現,并注意到了個人與社會的聯系。這為他日后強調人格的充分發展進而改造社會準備了思想認識。對舊事物的批判要求觀點的鮮明尖銳,對新思潮的紹介要求表達的明白曉暢,詩歌、小說等文藝形式顯然不適合于這一點。因此,張聞天最初發表于《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的文章以評論、雜感為主。他的第一篇顯示出文學色彩的創作《夢》發表于1919年8月27日的《時事新報·學燈》。
上海的《時事新報·學燈》和《民國日報·覺悟》作為“四大副刊”之一,是新文化傳播的重要陣地。茅盾曾提及,《時事新報》“‘五四’以前,對新文化運動持反對態度,其后急變而以提倡自居,副刊《學燈》曾在上海青年學生中有過一個較深的印象”。上海與南京相隔不遠,南京的青年學生同受其影響是毋庸置疑的。張聞天這一時期的創作主要發表在《時事新報·學燈》與《民國日報·覺悟》兩種刊物上。由于地緣關系,對于文藝特別愛好的張聞天寫出自己的第一篇文藝作品時,選擇兩者之一發表在情理之中。《時事新報·學燈》不斷變動的編輯群體,使該刊在不同時期呈現出不同的編輯風格。其中,1918年底《學燈》向新文藝的轉向與張聞天《夢》的發表有著重要聯系。
..............................
第三章到人生中去:做無私的光明的找求者
第一節“在社會主義的歷程做一個小卒”
文學論文參考
張聞天《無抵抗主義底我見》發表后,引來了陳望道、沈雁冰的批評,陳望道與沈雁冰都主張暴力革命、武裝反抗。1920年,陳望道協助邵力子,擔任《民國日報·覺悟》編輯一職。張聞天是《民國日報·覺悟》的熱心讀者,也是積極撰稿人,來往之中,兩人觀點上時有交鋒。同年,陳望道由日文轉譯了我國第一部全譯版《共產黨宣言》,思想上表露出強烈的馬克思主義傾向。陳望道撰寫了《怎能實行無抵抗主義呢?》與《論愛——答聞天先生》兩篇文章,回應張聞天關于無抵抗主義的見解。陳望道質疑了張聞天“現代的人竟無人格之可言”的觀點,提出能夠幫主人民排除痛苦的都是愛,“不抵抗善使善滋長固是愛;抵抗惡使惡消絕也便是愛”,“對于壓迫階級,抵抗便是愛;對于同階級或更下階級,協助便是愛”,主張暴烈抵抗是殘忍無愛的人,但主張弱者不抵抗,也是另一方面的殘忍。在沈雁冰看來,無抵抗主義是一種理想化的宗教思想,應對其應用范圍加以限制。“愛”作為一個抽象名詞能夠感化人,卻不能改造社會的組織和經濟制度。沈雁冰推崇蘇俄革命的道路,“就現在人類所能做到的事而言,這一條‘路’,已有那些被人稱為‘俄羅斯人’的‘人們’造下來了。”面對陳望道、沈雁冰的批評,張聞天寫了《人格底重要——答雁冰和曉風兩位先生》加以回應。張聞天一方面認為馬克思主義也存在局限,唯物史觀并不能說明全部現象,另一方面又聲明,自己并不是絕對主張無抵抗主義,若有更容易實現“愛”的方法,“我自然會拋棄我現在的主張追隨諸先生之后。”可見,無抵抗主義的主張對張聞天來說僅是一種可能“途徑”的選擇,并非唯一之“途徑”,當更有效的方法出現時,他可以隨時進行調整。
第二節投身革命洪流
.................................
第三節張聞天與左翼文學運動
........................
結語
張聞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身份為人們熟知,“五四”時期“文學青年”的身份卻往往被人忽略。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人生階段,早年“文學青年”的經歷,并非僅是張聞天政治生涯的簡單注腳,而表現出自身的獨特性。張聞天“文學青年”的角色與政治家的角色不是二元對立的,二者由此及彼的轉化,體現著不同時期張聞天在“途徑”問題上做出的不同選擇。作為“五四”時期青年知識分子群體的一種典型代表,被召喚到歷史現場的“新青年”張聞天走過了曲折的探索道路,受制于歷史與時代條件,他的思考與行動或許不夠成熟,卻反映著鮮活的時代精神與時代氣質,在其早期的文學活動當中,這一點體現得尤為鮮明。
“五四”時期,社會改造思潮在國內興起,農民、勞工問題等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問題。社會改造論者提出了不同的社會改造方案,并加以提倡與實驗。在張聞天早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社會改造思潮的鮮明影響。張聞天已經能夠從階級視角深入淺出地剖析社會問題,并希望以此引發民眾共情,達到“開導無知識”,即啟蒙的目的,最終實現“勞農界人起革命鏟除士大夫階級”。張聞天信奉無政府主義與新村主義,希望通過精神運動,幫助人們得到“愛”與“真生命”,養成健全的人格,完成內部精神的改造。他同時回答了“個人在社會中如何起作用”這一問題,主張改造完畢的完善的個人,進一步自由聯合成“新社會”。張聞天在創作風格上深受唯美主義的影響,他也譯介了許多東西方浪漫主義、唯美主義的作家作品。對愛與美的極端提倡,同是基于充分發展人生、培育健全人格的目的,以推進精神運動,實現“生之快樂”與“生活底變動”。
參考文獻(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