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論文:秦漢盜罪及其比較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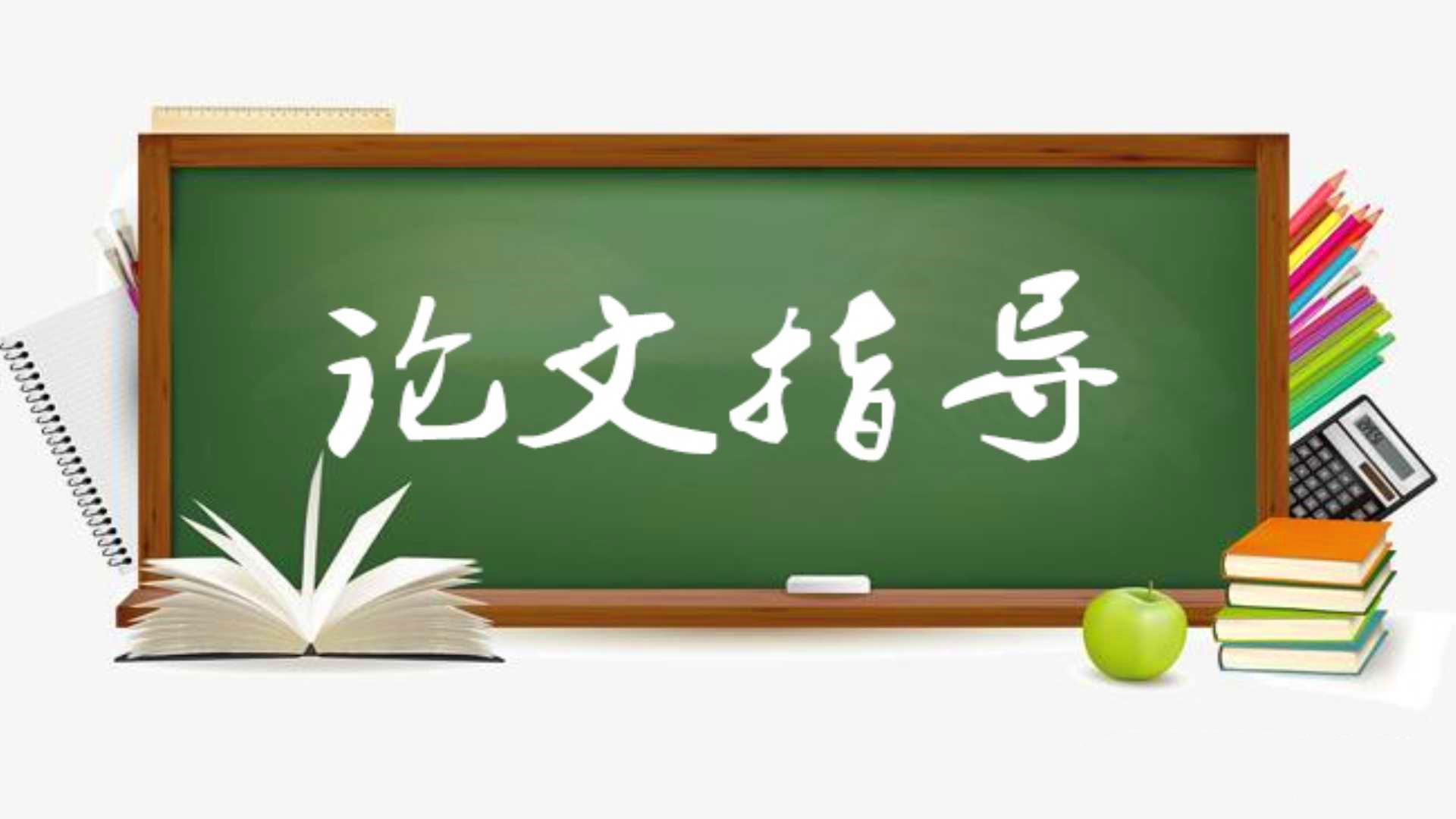
本文是一篇法律論文,本文通過對近年來出土的秦漢簡牘進行系統的整理分析,運用二重證據法、比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參考歷史文獻及學者著述,對秦漢盜罪的定義、構成要件以及刑罰規則等展開研究。
1 導論
1.1選題目的與研究背景
1.1.1選題目的
在對中國古代法制史進行研究時,學者們通常用大量的篇幅來對中國古代刑法制度進行描述,而簡牘文獻的出土,更是為中國古代刑法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近年來,伴隨著秦漢時期簡牘文獻的大量出土,學者們亦展開了對秦漢時期相關制度的研究,而盜罪作為最為重要的財產犯罪之一,更是學者們研究的重點。在現有對秦漢盜罪的研究文獻中,學者們研究的重點主要在于秦代或漢代盜罪制度的犯罪構成、秦漢簡中某一類型盜罪以及秦漢盜罪制度某些方面的沿襲等方面,缺少了對秦漢時期盜罪制度的動態發展以及兩者之間的比較研究和整體研究。此外,以往學者們在對出土的簡牘文獻進行應用時,往往也只涉及到出土秦漢時期的某些簡牘或簡牘中秦漢時期盜罪的某些方面,并不曾對簡牘中涉及的秦漢盜罪制度進行全面和詳盡的研究。在之前史料缺乏的時代,學者們并不足以窺探秦漢兩個時期的盜罪發展全景。但近些年伴隨著文獻的不斷增加,大量出土的秦簡如睡虎地出土秦簡、岳麓書院藏秦簡,大量出土的漢簡如張家山漢簡、居延漢簡以及新出土的東漢簡牘張家界古人堤遺址出土文獻等文獻的出現,其中所涉及大量的關于秦漢盜罪的律令和案例,為研究秦漢兩個時期盜罪制度及其比較提供了可能性,為秦漢兩個時期盜罪制度的發展及其比較研究提供了更廣闊的視野。
大量出土的秦漢簡牘得以讓我們窺見秦漢時期盜罪的重要性:一方面,秦、漢時期均設立了專門的官員、通過專門的法律對盜進行制裁和處罰;另一方面,秦漢時期還利用占卜對盜進行預測、抓捕,并將盜罪的量刑標準和處罰規則作為其他犯罪的評價標準。此外,盜罪案例還承擔著現代法律解釋的作用,官員們通過盜罪案例來解釋秦漢時期的刑罰原則。這些原則在朝代變更中保留下來,甚至在今天的刑法制度中仍然能看到其影子,如盜罪的量刑原則——平價原則。秦漢時期對于盜罪的打擊不僅涉及到國家對于民眾基本人身權和財產權的保護,還涉及到國家政治秩序的穩定甚至一個國家的存亡。本文在學術界已有研究的基礎之上,以秦漢盜罪作為研究對象,以已經出土發表的簡牘文獻作為基本材料,力圖對秦漢時期盜罪做較為詳盡的全面研究和比較研究,并擬解決以下幾個問題:秦漢時期“盜”的內涵?現代犯罪構成要件理論下秦漢時期盜罪制度的發展?秦漢時期關于盜罪的量刑規則?秦漢兩個時期盜罪之間的沿襲與發展?秦漢時期盜罪發生的原因?
.........................
1.2研究現狀與研究材料
1.2.1研究現狀
法學論文怎么寫
盜罪作為中國古代統治者打擊的重要犯罪,亦是后代法律史學者研究的重點問題。隨著秦漢簡牘的出土,從出土文獻資料出發對中國秦漢盜罪展開研究的學者亦不在少數。在對秦漢盜罪進行研究時,學者們多從以下九個方面入手:第一,考釋“盜”字的起源及發展,如王毅力的《常用詞“竊”、“盜”、“偷”的歷時演變》;第二,分析“盜”的稱謂及法律身份,如王子今的《論秦始皇出行逢“盜”及秦代“盜”的法律身份》;第三,分析盜的來源,如張功的《秦朝 “盜” 考論》;第四,對秦漢盜罪的犯罪構成進行研究,如張蘭蘭的《秦簡中的“盜罪”問題》;第五,通過簡牘對秦漢盜罪的沿襲繼承進行研究,如閏曉君的《秦漢盜罪及其立法沿革》;第六,對秦漢簡牘中盜罪的具體犯罪類型如群盜,官員監守自盜等進行研究,如黃海的《“醴陽令恢盜縣官米”案與漢代的官員監守自盜犯罪》;第七,對秦的連坐制與“與盜同法”、“與同罪”這種特殊牽連罪進行研究,如日本學者石岡浩的《秦的連坐制與“與盜同法”“與同罪”—秦法中的特殊牽連罪》。第八,對出土的秦漢監牘中的盜罪所反映的法律思想,法律原則等進行研究,如朱瀟的《岳麓書院藏秦簡<為獄等狀四種>與秦代法制研究》。第九,對秦漢時期盜的刑罰種類,量刑規則等進行研究,如彭浩,陳偉以及工藤元男的《二年律令與奏讞書》。
在對秦漢盜罪進行研究時,學者們對某些重點的問題存在沖突或已經達成一致,因此,在本文展開對秦漢盜罪的比較研究時,需要對學者們研究過程中已經存在沖突或達成一致的問題進行說明。
.......................
2 秦代盜罪研究
2.1秦代盜罪含義
在傳世的先秦文獻中,先秦時期的盜的含義并不明確,一般有兩種含義:一是可以指犯罪的行為,如竊取財產的行為、官員違反國家官吏管理秩序的行為以及威脅統治的政治犯罪行為。二是可以做形容詞,具有私下的、悄悄的含義。
“盜”在指稱犯罪行為時,其內涵以侵犯財產為中心,主要包括對三類財產的侵犯:1、對個人財產的侵犯,盜在表示財產性犯罪盜竊時,與“竊”意思通用,《說文·米部》:“盜自中出曰竊。”如在《尚書·費誓》中,就有“竊馬牛”的記載,根據顧頡剛、劉起釪兩位老師在《尚書校釋譯論四》中考證認為,這里的“竊”就是盜竊的意思。如一般主體通過竊取的手段侵犯他人財產的行為。2、對國家財產的侵犯,如國家官吏不當行為導致國家財產損失的行為。3、對君主財產的侵犯,主要是指威脅君主統治的行為,其原因正如莊子所論述的“大盜盜國”,將國家視為君主的財產,威脅統治的政治犯罪行為自然可以視為對君主財產的侵犯。《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記載了秦始皇在兩次巡游中遇到“盜”的情形,王子今在《論秦始皇出行逢“盜”及秦代“盜”的法律身份》中分析認為這里的盜不僅僅是簡單的盜竊財產行為,而屬于政治上的犯罪行為。此外,在秦代出土簡牘中,亦有與侵犯財產權益并不直接關聯的犯罪行為如官吏行賄、受賄等行為,但由于秦時期統治者并未對“盜”的內涵有明確的認知,而以財物為連接點將一系列犯罪行為囊括到“盜”罪下,本文亦將從廣義的角度對秦代盜罪進行研究分析。
...........................
2.2秦代盜罪構成要件研究
傳統上,法律史學者們在對出土的秦代簡牘文獻中盜罪的定罪量刑進行分析研究時,一般認為秦代是通過侵犯財產的數額來進行認定,從而決定是否構成盜罪以及適用的刑罰等級。近年來,亦有學者以現代的犯罪構成要件理論對秦代盜罪進行分析,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科學性。因此,為方便后文對秦漢盜罪進行比較研究,本文采用現代犯罪的構成要件理論對秦漢盜罪展開研究。
2.2.1主觀上區分故意與過失
在主觀方面,根據筆者對出土的秦代簡牘中涉及到盜罪的162條簡牘進行檢索分類,其中犯盜罪主觀是故意的簡牘有66條,主要表現為通過秘密竊取的手段侵犯他人財產,官吏管理不當、管理受賄等;主觀是過失的簡牘僅有1條,即關于“端”和“不端”的規定,不端則主觀表現為過失或其他。不考慮主觀因素還未見有相關簡牘。從出土的秦代簡牘中,我們可以看出秦代時期對于犯罪故意和犯罪過失有了初步的區分,并且已經認識到犯罪故意的危害,趨向于打擊故意犯罪。在秦代,犯罪主觀方面對于認定是否構成犯罪以及所受的刑罰程度是不同的。
在睡虎地出土秦簡的《法律答問》中,記載了許多關于秦代犯罪主觀故意的簡牘,主要集中在秦代關于誣告的規定中:“甲告乙盜牛若賊傷人,今乙不盜牛,不傷人,問甲可(何)論?端為,為誣人;不端,為告不審。”“端”即為故意,主觀上出于故意去誣告別人的構成誣人罪。“不端”即不是故意,主觀上可能表現為過失,則不構成犯罪而僅為控告不實。“端”的懲罰顯然是大于“不端”的。《法律答問》中記載的另一案件也說明了這一點:“告人盜百一十,問盜百,告可(何)論?當貲二甲。盜百,即端盜駕(加)十錢,問告者可(何)論?當貲一盾。貲一盾應律,雖然,廷行事以不審論,貲二甲。”誣告應當是貲一盾,但由于其主觀上是故意的,加大了處罰,變為貲二甲。在這兩條簡牘中,可以看出秦代時犯罪的主觀方面對于犯罪的認定與刑罰具有重要意義,而這一點也在盜罪中得到體現。《法律答問》中有以是否有犯罪故意來認定是否構成盜罪的案件:丈夫盜竊三百錢,告知其妻,妻和他一起用這些錢飲食,妻沒有在犯罪前與夫共謀的,以收贓論處;如妻與其夫犯罪前共謀的,與其夫同罪。丈夫盜竊二百錢,在其妻處藏匿了一百一十,妻如知道丈夫盜竊,應按盜錢一百一十論處;不知道的,以守贓論處。在這類案件中,妻并沒有參與盜竊,但是如果事先知道或在夫盜竊后明知其夫盜竊并一起使用了贓物,也要與其夫同罪,不知道則不構成盜罪,認定構成盜罪時強調其犯罪故意。
...........................
3 漢代盜罪研究
3.1漢代盜罪含義
.......................................
3.2漢代盜罪構成要件研究
...........................
4 秦漢盜罪制度比較研究
4.1從法律制度出發——制度上的差異性
4.1.1秦漢盜罪主觀構成要件比較
............................
4.1.2秦漢盜罪客觀構成要件比較
............................
5 秦漢盜罪制度發展原因剖析
5.1政治層面
法學論文參考
在通訊信息并不發達的秦漢時期,要控制人民以穩定自己的統治,最好的方法就是通過土地將人民固定下來,再通過制度規范人民的行為以達到對人民基本生存權利的保護。由于生產資料的缺乏,人民最基本的權利僅包括兩個:人身權和財產權。人身權的保護在秦漢律中已經有諸多規定,且有較為清晰的發展軌跡,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二年律令·賊律》一篇。對于財產權的保護,秦漢時期主要表現在對“盜”行為的規制上,由于“盜”的含義并不精確,“盜”行為并不是單純的侵犯財產的行為,而是一類以侵犯財產為核心的既侵犯單一客體,又侵犯復雜客體的一類行為。從對侵犯財產權利犯罪的打擊從而達到穩固統治的目的來說,秦代統治者主要從三個層面來進行:一是對人民基本財產權利的保護。出土的秦簡中有大量關于侵犯他人財產權利的簡牘,并明確規定通過贓物的價值進行處罰。二是加大對具有抓捕盜賊的官吏盜竊財產行為的處罰。在秦代這一時期,秦代統治者已經認識到具有職責的官吏犯盜罪與一般主體犯盜罪有所不同,對于國家政治秩序危害性更大,加大了對官吏犯盜罪的處罰。但是,對于官吏行賄受賄的問題并未有更多認識,僅規定與一般盜罪同法。三是加重對群體犯盜罪的處罰,主要就是群盜行為。在這一時期,統治者對群盜的打擊主要是出于對群盜行為所能引發的更大程度的財產損失和人身暴力進行的打擊,并未明確的認識到群盜行為可能轉化成為更大規模的政治犯罪,這一點從秦始皇兩次出游遇盜的行為性質可以看出。秦代時期對于盜罪的打擊主要是針對侵犯財產行為,其目的主要在于維護人民的財產權,穩固自己的統治。
5.2思想層面
...........................
6 結語
根據本文對秦、漢兩個時期的比較研究,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盜”的含義在秦漢時期指的主要是一類侵犯財產權的行為,但是其外延有所不同。在秦代,“盜”在法律上的含義主要是侵犯財產的行為,獲得財產的手段不僅包括秘密,還包括侵占、詐騙等。漢代在秦代盜罪是侵犯財產行為的基礎上,對“盜”的法律外延有所擴展,還包括對國家管理秩序,國家政治秩序的破壞。在該時期,統治者已經認識到秦代時期所規定的“盜”行為侵犯客體的復雜性,其危害后果相比單純的侵犯財產的盜行為更為嚴重。
與秦代盜罪的法律結構,盜罪的構成要件相比,漢代對于盜罪的規定也更加精細化。在法律結構方面,漢代將盜罪單獨規定出來,形成《盜律》一篇,減少“與盜同法”等的應用,法律用語更加精確,法律結構更加完善。在構成要件方面,漢代較秦代更加明確。在主體方面,漢代肉刑制度改革將秦代犯過罪的人逃跑的行為不再納入漢代盜律規制,漢代主體僅包括一類一般主體與一類特殊主體,增強了法律檢索與法律適用的可行性。在主觀方面,與秦代對故意與過失的模糊界定相比,漢代統治者已經充分認識到故意犯罪的危害性,出土的漢代簡牘未見有關于犯罪過失的規定,提高了盜罪的入刑標準,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漢代盜罪的犯罪率。在客觀方面,與秦代認為盜罪主要是對侵犯財產的侵犯相比,漢代統治者已經充分認識到盜罪侵犯客體的多樣性,對侵犯單一客體的行為一般打擊,對侵犯復雜客體的行為加大打擊力度。
參考文獻(略)



